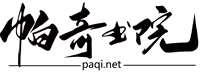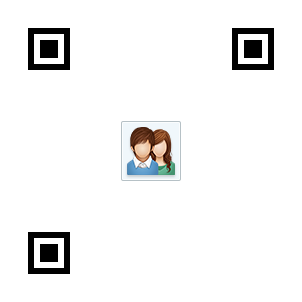蔡确左一句以国事为重,曾布又一句以国事为重。
章惇在旁摇旗,张璪则敲着边鼓。
可向皇后还是在摇头,不肯主动出面逼丈夫逊位。
“平章。”蔡确回头来找王安石,他实在不想找韩冈,也只能请王安石帮忙,“国事为重。都要四更天了,到了天明还不定下来,明天朝堂上会变成什么样?!”
王安石脸色并不好看,像是被人欠了钱——他还不在乎钱,应该是被人烧了满屋子的书那样的?德,则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。自然之中,只有弱者才会让出私物,狗埋骨头是为了什么,怕被抢!蛮夷心如禽兽,视人亦如禽兽,面对弱者,他们唯一会做的,就是欺上门来,不会有半点同情。就算中国再以德化待之,也只会被认为是畏惧,馈赐再为丰厚,也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。”
韩冈滔滔不绝的一番话,将进化论的一个变种送给了四夷。反正他们用得上。而无论如何,韩冈都不会将之用在自家身上,赤裸裸地宣扬弱肉强食,在儒家为根本的社会里,会没有任何立足的余地。但当今民间,弱肉强食却不胜枚举,任凭哪一个都能随随便便数出几十条见闻来。豪右世家兼并田宅,这不是弱肉强食还是什么?前几年京城粮商趁灾荒囤粮不售,打算牟取暴利,这不是弱肉强食是什么?
?再往下的道路边,还能看到一座草房的地基,那是军巡铺。从瓶形寨出来的逻卒在国界上一圈绕下来,都会走到这里。在太平时日,肯定也会供往来的客商歇歇脚,喝水吃饭。
河东边境城寨外围的烽燧,只要靠在官道边,多半如此。七八个人一队,驻守在这一座烽燧中。同时照看着路边的递铺、巡铺。
不过这座烽燧,现在没有士兵在上面看守,空荡荡的,几条竖起的旗杆也看不到一面旗帜。烽燧的一边外墙上残留的箭矢,密得像是刺猬的后背。
“神臂弓。”音量极低地喃喃自语,除了韩中信本人,没第二人听得到。
入寇的辽军得到了代州?面低调一点就可以了。
蔡确、曾布他们,肯定也是不想看到自己忙前忙后,跟他们抢生意。
“玉昆你是站在高处不怕湿脚。”薛向的低声一句,也不再多说什么了。
薛向也不急。当初冬至夜时,他好歹也是第三位请立太子的宰辅。从时间上,比王珪早一步,从表现上,比王珪好得不只一点,就性质而言,他是功,王珪是过。
有这一份功劳,现在也不用跟人争抢了。也就是当初排第二的张璪,就稍嫌贪心了一点。估计是想做宰相,以他的情况,也只有积累定策之功才有一星半点的机会。
看着蔡确和曾布的表演,韩冈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夜?过去,却是容光焕发,仿佛换了一人。
韩冈打了个哈欠,一下子坐了起来,“在外半年,就没有个舒心的时候,为夫也只是将欠下的补回来。”
王旖对着梳妆台上的镜子,轻轻地扑着粉,小声嘀咕着,“谁知道官人你在外面有没有养着?我们闷在家里又不可能知道。”
“看来昨夜没说清楚啊,要为夫现在再解释?当如此,可奈何?”
皇权才是第一位的,纵使父子之亲也抵不过权力的诱惑。同时让国家顺利传承,也是对赵氏天下的恩德。只要明天赵佣顺利登基,成为大宋的第七位天子。这拥立之功,就是明明白白,谁也否定不了了。就算赵佣日后心中还有着疙瘩,但终究还是不能恩将仇报。
为国无暇惜身,得利的又是太子,怎么也不能说他们是叛逆吧?
所以他们不怕急,只怕慢。
帝位传承上,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祸。谁敢保证一点意外不出?就是万分之一的危险,也没有哪个宰辅愿意去冒上半点。
看着面前的几位宰辅,一张张急切的脸,再看看在后面肃然默立的薛向和韩冈,向皇后撒气一般地道:“罢了,罢了,国事就国事吧,这名声我也不要了!”
皇后终于松了口,蔡确、曾布等人大喜过望,赶着遣人去玉堂找值日的翰林学士写传位诏书。
“事不宜迟,迟则生变。明日早朝时,就让太子上殿。”
“衣服呢?”章惇突然想起了一件事,“太子还没有衣服啊!”
章惇的话听起来有些好笑,但每个人都明白他想说什么。太子的衣服多得穿不完,只是没做皇帝时穿的衣服。
登朝总要一身冠冕。
新帝登基之后,面见群臣,肯定不能再穿着亲王的服色。天子六服,六套用在各级典礼上的不同舆服。都做了皇帝,不能说衣服都不够在大典上穿吧?
“舆服怎么办?现在做还来得及吗?”曾布也慌了起来。
大宋开国一百多年,几次天下易主,新帝都是因丧即位,没有说老子还在,儿子直接就登基的。这内禅的礼仪,谁都没经验。现在忙得乱了套,要是赵佣穿了一身皇太子的服色上殿,让群臣朝拜,那就不是内禅,是笑话了。
连王安石在内,宰辅们都皱起了眉。所谓量体裁衣,这时候哪里来得及招裁缝来量了尺寸,再去裁剪、缝制。又不是秃驴们的一口钟【注1】,两块布缝几针就能穿上身了。那是天子舆服,耗费多少人工和心血都是应该的。
若是正常的父死子承,新皇帝就要在梓宫前麻衣素服,不冠不冕,甚至披头散发,捶胸顿足,以示心中的哀恸之意。三辞三让,不用急着穿上礼服。有足够的时间制作新衣。以一干专为天家服务的宫廷裁缝的手艺,要把天子所用的袍服都做好,也不过一两天的事。只是现在只剩下半夜时间,哪里还来得及?
“已经做好了一套。”皇后忽然说道。
殿中陡然间就静了。
刚刚还很兴奋的蔡确和曾布,就像是被冰水淋头,一下都僵住了。
韩冈都不由得直了腰,惊讶地望着向皇后。
“去年官家中风后,清源郡太夫人入宫,劝吾说官家得天佑,当无大碍。但事有万一,还是稍作准备,缓急间也不会误事。这话吾觉得是有些不好听,可终究是忠言,所以吾就让人去做了一件预备着。”
皇后惴惴不安,毕竟方才还议论得热闹呢,现在却一个个都噤口不言,瞪着眼,让她也感觉有些害怕。
不过皇后解释了之后,冰结的空气就缓和了下来。
宰辅们都反过来看蔡确。蔡确虽为宰相,可惜年资浅薄,尚未得封国公,依然是清源郡公。而清源郡太夫人,便是蔡确的老母明氏。
什么时候就打了钉子下去?皇后不说,还真是不知道。
韩冈看蔡确的表情,似乎也是吃了一惊。估计是没指望他让他母亲出的提议,会被皇后听从。
“先不管那么多了,得赶快找人取来。”蔡确有点狼狈地大声道。
章惇抬手压了压,示意少安毋躁,问向皇后,“殿下,做好的是哪一套?”
“通天冠、绛纱袍,哦,还有一套赭黄袍的常服。不过这半年,太子又长高了点,可能穿不下了。”
张璪松了口气,“那就是两套了。”
韩绛皱眉道:“至少应该做一套履袍才对。就仅仅是绛罗袍,绛衫袍也行啊。”
正式的大礼服,是大裘冕和衮冕——玄衣、纁裳,以黑色外袍和赤黄色衣裙为主色。次一级的礼服,是通天冠、绛纱袍,是正红色。再次一级,为履袍,黑革履和绛罗袍,衣服颜色依然是正红色。直到作为常服的衫袍、窄袍,才有赭黄、赤黄、浅黄为主色的袍服,同时依然有绛色的衫袍。
所谓明黄色的龙袍其实于古礼不合,在等级比较高的典礼上,并不会出现。只不过一年三百六十天,能有大典礼的次数实在不多。绝大多数时候,还是以衫袍、窄袍为主,天子服黄的情况也就很常见。
“有赭黄袍也够了。也不是没故事的。”
蔡确没明说出来,但大家都明白。
没错,的确是有先例——太祖皇帝。陈桥驿黄袍加身嘛。天下谁人不知?
天子六服中,通天冠、绛纱袍排在第三等,履袍则是第四等的礼服,赭黄袍则更差一级,前两件在登基大典上都能用得上。但勉强点,赭黄袍照样能用。反正只要主要的礼服不出问题就行了。
这就跟结婚一样,连鞋子带衣服,要一套套地换。没有说一件从头穿到尾,其中错一点也没什么。只要接亲和拜天地时的衣服不错就行了。
朝廷的大典礼,只要皇帝主持,基本上都是一身接着一身地换。虽说是礼制,其实也害人。去年郊祀,如果赵顼坐在玉辂上时,也穿大裘冕,或许就不会中风,毕竟外面还有一件黑羊皮的大裘可以防风御寒。可惜按照礼仪穿的是通天冠,外套一件绛纱袍,从里到外透风。
不过现在是有什么就用什么了,还能有什么挑拣?
“事已至此,也只能先凑合着用。赭黄袍就赭黄袍。有通天冠、绛纱袍,御正殿时能用了,其他时间,则穿赭黄衫袍。”
“那大小呢?”
“改衣服容易,量了尺寸,在这里就能改!”
“量尺寸……得将太子请来了!”蔡确连忙道。
忙了一通,这才发现,他们将主角给忘了。
现在就要内禅,主角不能不来!
注1:一口钟,指一种无袖不开衩的长外衣,以形如钟覆,故名,又名“斗篷”、“莲蓬衣”、“一裹圆”。